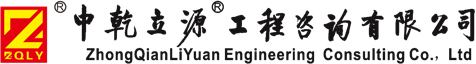当盛唐的钟鼎之声渐次响起,当长安城内的权力盛宴如火如荼,一位身着紫袍的宰相却在帝国的政治中心写下了一系列看似不合时宜的诗篇。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如同繁华盛世中的一泓清泉,以"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的素净之姿,对抗着一个日渐浮躁的时代。这些诗作远不止是官场失意后的情感宣泄,而是一位儒家士大夫在权力场域中艰难守护的精神自白,是盛唐气象背面那个被遗忘的清醒者的低语。
张九龄的政治生涯几乎与开元盛世的黄金时期重合。作为玄宗朝最后一位贤相,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唐王朝由治入乱的微妙转折。《感遇》的创作背景极为特殊——它诞生于诗人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却又预感危机将至的时刻。与陈子昂的《感遇》不同,张九龄的诗中少了几分慷慨悲歌,多了几分从容不迫的智者风范。"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样的诗句,不是怀才不遇者的牢骚,而是功成名就者的自律宣言。在权力与道德的天平上,张九龄始终保持着令人惊叹的平衡能力。
《感遇》组诗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精神贵族主义。张九龄以兰桂自喻,却超越了简单的比德传统。"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中的"林栖者",暗示了一种超越功利的精神知音;"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则以南方嘉树的耐寒特性,象征士大夫在政治寒冬中应有的节操。这种贵族精神不是门第意义上的,而是道德与智性层面的自我要求。